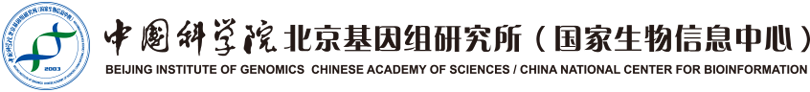我和诺奖得主托马斯林达尔(Tomas Lindahl)的师生情缘
北京时间10月7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了201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名单,来自瑞典的托马斯?林达尔(Tomas Lindahl)、美国的保罗?莫德里(Paul Modrich)以及土耳其的阿齐兹?桑贾尔(Aziz Sancar)共同获得这一殊荣,以表彰他们对于DNA修复的机理研究。他们发现的DNA修复机制理论很早就延伸到癌症治疗中,为放化疗提供了理论指导。
得知托马斯?林达尔获得诺奖的消息,我的心情异常激动,因为获奖者是我师从三年的导师。此时此刻,往事如潮水般涌来。2000年,我从中科院上海分院博士毕业后,在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教授的推荐下,来到法国里昂,在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在那里的“国际癌症研究署”开展博士后科研训练,师从欧洲科学院院士汪兆琦教授。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肿瘤基础研究中常用的模式动物小鼠,并第一次了解到DNA损伤修复的概念。
说起DNA损伤修复,不得不提到被誉为“DNA损伤修复之父”的托马斯?林达尔。自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人们一度认为DNA是固定不变的结构。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托马斯发现,DNA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稳定,在紫外线、自由基及其他外部条件影响下也会发生损伤。托马斯的贡献就在于率先观察到了DNA的降解和损伤,打破了科学界一直认为DNA双螺旋结构极其稳定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的发现了DNA存在修复的机制。
因为上述原因,我产生了想去托马斯?林达尔教授实验室继续深造的想法。彼时,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在汪兆琦院士的推荐下,2005年9月,我获得了前往托马斯实验室面试的宝贵机会。在飞往伦敦的航班上,我的脑子里时刻想象着这个被称之为“DNA修复的圣地之一”的克莱尔实验室(Clare Hall Laboratories)会是什么样?托马斯又是一个怎样的科学家?直到司机把我从机场接到了实验室,我才异常惊讶地发现,克莱尔实验室竟然位于被田园包围的伦敦郊区,寂静无比。第二天在实验室第一次见到托马斯,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热心地安排我和课题组成员以及多名教授交流,带我参观实验室,让我感受到一种追求创新和合作的一流学术氛围,我想加入托马斯团队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还记得当晚托马斯邀请我到餐馆用餐,点的是淡菜(也叫海红)。回到法国之后,我收到了托马斯的电子邮件,他热忱地欢迎我成为他的最后一名博士后,也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关门弟子”。

被田园包围的克莱尔实验室
但是到了真正做决定从福利待遇不错、气候优越的法国里昂搬家到待遇较低、经常下雨且物价昂贵的伦敦时,对一个有着两岁孩子的家庭来说还是具有很大挑战的。我的太太宣琛和在国内的亲人此时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支持,让我下定决心奔赴伦敦。2005年11月,我正式成为了托马斯的学生。而那时,托马斯已经68岁了,马上要从研究所所长岗位退居二线。退居二线后的托马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实验室,而我对他的真正了解也正是从这段时光开始的。
在与导师相处的这段时期,我们讨论最多的除了科学还是科学,让我时刻感受到一个老科学家对自己所热爱的科学那份执着的情怀和不知疲倦、孜孜以求的精神,也分享了他当初发现DNA损伤现象以及修复机制后的兴奋之情。他的同事蒂姆.亨特(Tim Hunt)(2001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评价他对科学的热爱和激情是永无止境的。我对此极为认同。
在外人眼里,托马斯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但实际上他同时又是一个诙谐幽默,丝毫没有古板气的绅士。他常常与学生开玩笑。记得那时我经常和他在单位食堂吃午饭,有几次当我和托马斯买了同样的牛排时,大厨往往给我的要小一点,而给托马斯的牛排一般都比较大。托马斯幽默地解释说,可能是厨师认为他高个头需要的能量多,而我小个头需要消耗的能量要少一点。
在科研上,托马斯对我要求很严格。但在生活中,他却时时关心着我。他知道我带着一家三口在英国工作很辛苦,虽然我从没有向他抱怨过物价贵,但他还是破例为我加了工资,并且告诉我要保守这个小秘密。
托马斯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学术好导师,经常安排学生参加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原创性科学思维和抓住新事物的敏锐力,对学生们的科研生涯影响深刻,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成为了富有成就的科学家。由于在他的研究团队,很多课题方向都是原创性的,没有现成答案和线索,因此做科研经常会碰到困惑和难题,有时会感到沮丧。托马斯会鼓励我们:“如果一个问题你查遍所有科学文献,也没发现目前有效的解决方法,那么在你自己的深度思考以及与领域其他专家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可能会形成一个好的科学问题,而这正是你值得去尝试的地方——如果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别人早就解决了,也无需你去解决。”而当学生取得成就时,他又会告诉我们:“任何成果,要继承性发展,不要总是回头看,多想想下一步!”托马斯为人严谨,不仅体现在对科学实验和科学数据的严谨,他对自己的权威和能力审视更加严谨。他经常对我们说:“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一定要去求证——我毕竟年纪大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下降了。”

2007年11月30日于伦敦,我和托马斯,贝弗莉参加110周年英国皇家学会年会
托马斯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管理者。他领导的克莱尔实验室一共招收了不到20位独立研究员,但25年的时间就成为了核酸生物学研究领域的顶级实验室,产生了10多名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两位诺奖获得者(蒂姆和托马斯)。蒂姆评价托马斯的成就时曾总结说:托马斯的科学成就除了他自己在DNA修复机制的杰出科学发现,还应该包括那些在他领导和指导下的优秀学生和同事取得的杰出成绩,也是托马斯成功的一部分。
2008年11月,我将结束在托马斯实验室的博士后生涯,在面临未来抉择时托马斯告诉我,“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基因组学,建议你结合分子和基因组学新手段;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你能够有所作为”。他的建议和我国内导师杨胜利院士的建议不谋而合。因此,我决定回国发展,来到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回国临行前,托马斯和他太太贝弗莉(Beverly)盛情邀请我一家三口去他家做客,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了美味的香草烤多宝鱼,并把他研究方向的实验材料都给了我,希望我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研究。
作为他的关门弟子,我在延续托马斯的DNA修复研究基础上,决定再迈进一步,开始研究遗传物质DNA释放基因信息的中间载体RNA修饰的可逆性。在托马斯的支持下,通过与芝加哥大学何川教授合作发现了RNA主要的化学修饰甲基化m6A(6-甲基腺嘌呤)修饰酶,证明了RNA化学修饰的可逆性,及其调控RNA加工代谢的重要功能。从当初建立实验室到如今的一些科学研究方向和细节,托马斯一直站在我身后,支持着我。

2008年11月20日于伦敦,托马斯、贝弗莉邀请我全家做客
退休后的托马斯,虽然已不再从事一线科研工作,但却经常为国际著名科研机构提供指导、咨询和评估意见。回国之后,我曾三次邀请托马斯到访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指导,他于2009年成为基因组研究所学术刊物Genomics,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GPB)编委,2010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海外特聘研究员;2013年,他的学术成就综述以“My Journey to DNA Repair”为题发表在GPB。2014年,托马斯来到中国参加“第四届DNA损伤应答与人类疾病国际研讨会”时,曾向与会者高度评价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中取得的进步。今年6月,我和师兄安恩(Arne Klungland)教授在挪威成功组织召开了“Tomas Lindahl Conference on DNA repair(托马斯?林达尔DNA修复会议)”。

2009年10月21日于北京,托马斯与我的研究团队

2015年6月20日,托马斯,安恩与我在挪威奥斯陆
回顾当年,我非常感谢我的博士和博士后科研生涯中的三位导师,他们分别是杨胜利、汪兆琦和托马斯?林达尔。他们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灯塔,照亮着我前方未知的科研路。
最后,我引用托马斯的一段话来结尾,印证诺奖得主托马斯其实是个科学老顽童:“我仍然非常享受做科学研究。这是非常令人愉悦、有趣和刺激的工作。它在不断的变化中前行。我愿意继续为科学工作上百年,见证它的不断发展”。(I still enjoy very much doing science. It is pleasure, it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it is stimulating. It changes all the time. I would like to be here around hundred years to see how science develops.-My Journey to DNA Repair)
我相信老人家的愿望一定会实现。